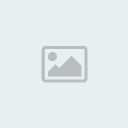
山木与鸣雁
——略评薛仁明《人间随喜》
——略评薛仁明《人间随喜》
记得儿时在四川老家,邻居家办丧事,常叫做办“白喜事”。年幼懵懂,一直搞不清楚为何死了人,还得叫喜事?老北京话里,也称福寿全归之死叫“喜丧”。很多人坐在灵堂里吃喝、打麻将,欢声笑语地守夜过头七。后来真遇到身边有什么人去世,我则会忽然哭,或忽然笑,也是不一定的。哀伤时没时间去想太多文化问题。但中国人即便对死,也可以围炉笑谈,应是无疑。朱耷笔意“哭之笑之”,弘一所谓“悲欣交集”,皆尽在此不言之中了。因世间法并无定理。万事都不能落入观念之窠臼,无论来自传统还是来自西方。
常人多分不清喜气与痞气的区别,正如很难区分来自良知的怒气与戕害精神的戾气之间的区别。罗汉在笑,牛二也在笑。死的悲伤,或《周易》“生生不已”的思想,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阴阳。且这世界太复杂了,除了欢乐,也需要一些“澄清天下之志”——即便这志气只是打扫一下自家的厨房和庭院。当然又不能执著于那些“有室荒芜不扫除,曰: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”之类的空话。
我说这些,是因为这初秋时节,正捧读吾友薛仁明君寄来的新书《人间随喜》。闲坐小窗,令心境豁然,忘记了暑气烦闷。因书中气息,与薛君之前的《天地之始》《孔子随喜》《万象历然》等可谓一以贯之:即依旧那么地博览世间草木,点染文字生涯。尤其他也大量谈到了中国人关于生死悲欢的差异。当然此书还收录了薛君近两年来的几十篇报刊杂文,讲座记录,以及与友人之对话(附册),内容从孔孟、庄子、诗经、刘邦、星云法师与死刑等,一直谈到黄仁宇、宅男、IPhone、隐性台湾、零体罚的教育、李登辉的“民主”、倪再沁的艺术、梅花、京剧、华夷之辨、礼乐制度、敬字亭、日本枯山水、胡适、南怀瑾、三国、儿女、师生传统、游春与读报、食养山房……不一而足,又满纸都是“薛风”之骨意。
老子云“静为躁君”。薛君书中最让我喜欢,便是他的静。诚然,这与薛多年来“熟读胡兰成,拜师林谷芳”有关,也恰恰与他说他早年也很激烈躁郁有关。他是“山野里走出来的读书人”,自然少了城市里的喧嚣味。他长在台湾,也自然没有大陆集权式的焦虑。他也曾徘徊孤愤,如今终于明了些什么。也因此,薛才会鄙薄“大陆学人受宋儒影响太深”,拘泥于愤懑。因近年来大陆之行,他见大陆读书人,脸绷得太紧,多数皆不快乐,或过于纠结于国家制度之事,总是想“以天下为己任”,故难以达到儒家或禅宗的那种自由喜悦。(详见薛《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》一文)。然即便是宋儒,也未必都是愤懑。如薛君文字,便可用宋儒邵雍之诗来形容一二,诚所谓:“松桂操行,莺花文采;江山气度,风月情怀。借尔面貌,假尔形骸;弄丸余暇,闲往闲来”。邵雍的居所名“安乐窝”,可见即便宋儒也是爱安乐欢喜之心的。
但在资本主义的现代,所谓“无利不起早”,我们真的能闲往闲来吗?
薛君最在乎的,便是中国传统之兴、乐、或“《论语》一开头,就是‘不亦说乎’、又是‘不亦乐乎’”与朝气等气质。书定名为“随喜”,也不仅是试图想传承胡兰成《心经随喜》的语境,更是想自身也有一种难得的欢乐之闲情。我略屈指了一下,薛在整部书中,提到此问题大约有二三十处之多。可见他深有所感。
不过,因薛太重视此现象,或许他也进入了另一种“因众人不快乐而吾即不快乐”的思维窑变之中了,也未可知。因为若按照“随喜”的逻辑,即便世间人尽都愤懑暴戾,我也该全然不管不顾,自行去不亦乐乎才对。正如道家所谓“逍遥”,禅宗所谓“无言”。何必还要为此耿耿于怀,著书立说,乃至为此四处游走布道?(薛不喜欢说演讲)。薛君常引不少庄子之语。因此,我忽然也想起了庄子的《山木篇》来。山中的大树因枝叶盛茂,伐木者都不砍,因为拿来无用。而去农家,主人杀雁请客。大雁其一能鸣,其一不能鸣,杀哪只呢?主人曰:“杀不能鸣者。”于是弟子们问庄子:山中大树,以不材得终其天年;主人之雁,以不材死。那我们到底应该做有用的人还是无用的人呢?庄子笑曰: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”。此语广而言之,便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,孔子欢喜朝气与宋儒式的悲哀暮气之间,传统的喜气与大陆的戾气之间……而大雁之鸣,堪比近代国人学者常有为世道“鸣不平”的行为。因为有太多的鸣不平,便有了薛君所言之戾气,学者们紧绷的脸,对儒家的误读等。
薛君希望“让孔子出土”,让大家都跟他一起欢欢喜起来。
而当这希望太大时,几乎让他又陷入新的忧虑了。
隐居十多年后,薛终于还是走向了写作、论述与行路。或许这就是天性吧。好在先秦也有墨子之苦行。孔门也有子路洒血、子贡庐墓、曾参每日三省、澹台灭明自立门户。《诗》也云“知我者,谓我心忧”。《礼》所谓“毋不敬,俨若思”(俨,正颜色也)。胡适曾说儒家是“信仰文字的宗教”,故儒家也有“仓颉造字,天雨粟,鬼聚哭”,也有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(苏轼),也有“书生好杀,时势使然也”(曾国藩)等深入骨髓的概念。佛教虽以拈花微笑为教外别传,但也有“愁面观音”或“十二头陀行”,以生厌离之心。所谓慈悲,也不能完全只是慈与善之随喜随缘吧。因这世间,有些人以乐为苦(哲学家),也有些人以苦为乐(苦行僧)。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与尼采的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,骨子里都是“随喜”这枚硬币的两面。而悲,也有与众生疾苦一起去悲悯、悲哀与悲恸之意。且晨钟之朝气,或可出盛唐气象,而暮鼓之暮气,也能出魏晋风度。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太多驴鸣、长啸、大哭、自渎、嘲讽、苦修与疯魔之激烈性情事,未必就不能启迪禅宗或心学的兴盛了。如整个中世纪的黑暗暮气和宗教昏聩,才恰恰让欧洲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。而整个先秦诸子,之所以有那样的生龙活虎,并不全是秦汉的朝气,也来自东周末期宫廷暮气的熏染罢。如“诸子皆出于王宫”之说(近代章太炎与胡适曾为此有过争论)。胡兰成在《闲愁万种》中也特别提到此语的重要性,说出于《史记》,其实此概念应出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民国五四的朝气,骨子里其实是来自晚清士人对帝国的惆怅。而胡兰成对自己,则干脆总结云:“我就是一败”。这是多么有“暮气”的惊人之语。
真正的大自在,大欢喜,应不偏不倚,阴阳调和,如“无立足境,是方干净”。
再者,文化分了东西,分了悲喜,就如智慧分了古今,首先便输了一筹。朝气或暮气,不在气本身,关键还是在望气之人与望气之用。
人心若对了,朝气与暮气,便都能有真气。
读薛君文字,便如这种对心自照。因在我看来:修、行、悲、喜,都是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和人生因素。一个人若从未快乐欢喜过,固然非常的不幸;但若是一个人也从未哭过,从未矛盾过,从未因爱或思想苦闷过,哪怕是一种“为了欢喜的苦闷”,凡事都没心没肺,那也是很无趣、很可怜的事吧。何况你若经过了那些尸横遍野,亲友们皆死无葬身之地的淆乱时代,难以释怀的残酷历史,便知道那不是用任何文化传统的乐观诠释和人生境界,便能消解的(如兰波云:“这一切不过是文学”)。因浩若烟海的生与死,爱与罪,都早已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事,而是对整个人性的反馈。但也好在有了薛君这样的人,这样的书,仿佛一部“山木与鸣雁的对话录”,我们又能为这文学之外的人生,找到一份真正无悲无喜的安心。且在我看来,或赤脚狂奔于荒野,或淋漓精致于暴风雨中,或在雪地里仰天长笑,或在夜读中拍案击节;宁静或冲动,血性与宽容,皆如隐月幽花,素琴残卷,国恨家仇,饮食男女……这些都是饱满鲜活的人生常态。菩萨心肠与金刚手段,二者缺一不可。正如随喜固然重要,但对悲天悯人时也须在所不惜。因为所有一切都是要入它们自己的渺茫大化去的,不必刻意厚此而薄彼呀。
2012-9-2
由杨典于2012-09-08, 09:06进行了最后一次编辑,总共编辑了2次

 11111.jpg
11111.jpg 

» 人生在世,所为何来?(空我道旨要)
» 以茶送走的一天
» 较量:中国和日本的第一首白话诗
» 即兴《无题之诗》(朵渔诗集《最后的黑暗》悦读中。。。)
» 我的宇宙观:创一新字,代替老子的道,成就我今生的修行
» 四滴茶
» 女史(二十六):茅司
» 一首好诗的凄美传说
» 逍遥谷游心录
» 随身卷子(乙本)1
» 钟颂——悼念广陵琴家林友仁先生并记二三事
» 薛仁明: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
» 新书《随身卷子:百衲本笔记野史、诗、念头与妖灯鬼火录》出版、目录、序言与预售地址
» 单鹄寡凫——汉人刘歆与宋人虞汝明对琴史的误读
» 展览馆不会空空的
» 十三首摇荡心目的微型诗
» 《知觉》2013年8月刊总第23期